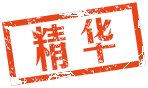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落拓 于 2024-9-6 16:16 编辑
1.
“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将啤酒灌满整个游泳池!”
我进门听见大声吆喝的禹加便知道他醉了。老板海生从吧台里冲出来将我像外宾一样请到禹加身边的长脚椅上。八罐阿姆斯特丹算六罐的钱得了,你快带他走吧。海生一边说一边吩咐人赶紧清理呕吐物。这个夏天里已经是第四次了。
我抗着禹加走在深夜两点的中山北路。他边晃荡手边唱“我爱你,我爱你——祖国”。要不是身上的钱全掏在了吧台上我还真舍得搭车回公寓,哪怕起步价是十元。
刚把他扔到沙发上便莫名其妙的清醒了似的对我说,真对不住你啊,兄弟。我将烧好的水灌进热水瓶里。他看见我没搭话便继续说,这日子真tmd难受。快,擦把脸。我扔一毛巾给他。禹加躺在沙发上把毛巾盖在脸上说,如果有人肯养我,哪怕是男的,要我怎么样都行。我一把扯过毛巾,我的工钱都被你丫的喝光了怎么没看你听我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呵呵笑到。说白了,这是禹加的口头禅。
2.
我有位在书店里认识的女朋友叫苏乙。她整个人唯一的长处就是身材够匀称,还有便是她对我言听计从。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出任何让我动心的地方。至少我认为是这样。长相一般思想单纯剪学生头穿十四岁少女都不穿的衣服用酷狗的文具说话细声细气而且太保守。禹加常说我之所以不喜欢她是因为她不肯和我做。我说你臭小子懂个屁啊。然而事实上是我对她没有一点冲动。
我们仍维持这种关系是因为我对女性有一种莫名的愧疚感以至于我无法做出令她们难过的举动。我无法知晓这种念头的来源,或许只是我已在不经意间把某些事件溶进了硕大的灰黑旋涡里。我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诡异的意识谋杀。
南西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看你应该和苏乙分手。禹加喝完最后一小口面汤突然说到。
我耸耸肩,表示我无可奈何。
要知道我无法按自己意愿去做会令别人伤心的事,尤其当对方是女人。
呃。禹加用舌头舔了舔上唇,的却,人可以有许多方式生活的,而最难的一次莫过于自己的方式。
谁说的?
书上看的。
关于禹加话除了那句口头禅外,他能说出的所有带些须哲理意味的句子几乎都是从书上搬来的。这点很容易让人看穿。况且这次他搬的如此生硬。
3.
苏乙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大三生。因此她太多理性而使她看上去太不性感。要知道相比较一个坐在你身边说三个小时世界观的女人,男人则更喜欢偷瞄穿比基尼的辣妹哪怕只有三秒钟。禹加对此观点深表赞同。
有时周末苏乙会到我公寓来充当没工钱的临时清洁工。之后我会请她吃廉价的快餐然后再去租盗版光碟来耗过整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等她挑完碟后主动付帐。她会将要租的碟向我征求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她看的东西都纯的保证我会有良好的睡眠。我付完押金然后上楼,开门,开电视,放碟,坐下来,看碟。像既定的程序毫无浪漫可言。我找来毛毯企图再度催眠。然而这次却让我格外清醒,甚至是清醒地让我越发认清自己丑恶的嘴脸。我对女性莫名的愧疚感使我无法平静地看完任何一部女性电影,更何况是阿尔莫杜瓦这个对女性世界理解充分的西班牙导演。他的影片会敏感的让我如坐针毡。
我逃到阳台上喝酒。等我把阳台上仙人球的刺数了十七遍的时候苏乙躺在我床上说她累了想睡了。我一看天色也不早了便劝她回宿舍,年轻女子夜行很危险。
“可我,今天就,想睡这,我……”她低头支吾着。
“快,起来!”我一把将她从床上拉起来,“这太不适合了!孤男寡女的对你名声可不好!”说着便将苏乙往门外拉。
禹加正好回来,手里抱着一箱啤酒。“你们俩干嘛呢?”他说。
苏乙使劲挣开我的手哭着离开了。
我未觉得我伤害到她某个痛处。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禹加,他做出一副与我无关的表情。
4.
一大清早我便打电话到苏乙宿舍。接电话的是一个有着江浙口音的女孩。她说苏乙不在然后挂掉了。语速快得几乎她正忙的不可开交,脑中浮现出接线员忙碌的场景。
我继续给禹加打电话。我想他八成又坐在酒吧里守株待兔,我总说他像个男妓。可这次接电话时他说他很忙要我长话短说。真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大家都工作到亢奋状态。
“下午六点回来。”我想这句话短到足以表达我的意思。
知道。他也简短地说两个字挂机。
其实我是想让禹加马上回来帮我搞定苏乙的事情,不过话到嘴边却窜了味儿。我口是心非地让他六点回来,不过具体要干什么我倒是没想好。也许我该像所有人那样在今天忙碌起来。扭头觑一下日历,6月17号,似乎没什么特别忙碌的必要。
5.
认识禹加是在六年前刚进大学时的校庆活动时。我坐在台下看高一届的禹加演奏歇斯底里的摇滚乐,这个节目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禹加在表演结束时疯狂地砸乐器更成为校内讨论的焦点。我说,这小子怎么这样?旁边有人说,他家是暴发户,有的是钱。而我并不是说这个,我只是不满他把我喜欢的歌手的照片贴在屁股上。
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学期我听别人说禹加他家破产了。
真正和他开始搭上话是在得知他要租公寓后。当时我的父母所乘的客机失事。作为法定继承人的我得到一笔慰问金和一小笔不算少的遗产。房子让我一个人住实在浪费于是便在学校的公布栏上用红纸贴着租房消息。当天晚上禹加便来了。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狂妄,与他相比我反而显得别扭。
很快我们成了朋友。而我则渐渐的从父母逝世的阴霾中走了出来。第二年我突然发现我请回来一个少爷。不但免收房租还要帮他付酒钱。
我们两个学着毫无用处的学科。他学的哲学让他糊里糊涂的只会整天念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的新闻学也无法让我找到个好差事,平时也只得无聊地写些风花雪月来骗取可怜的稿费。
禹加问我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
我说谈过。
“那你一定没同他们睡过。”
我想摇头,脖颈却僵在那里。“有倒是有。而且记忆深刻。”
“可否说说?”
“未尝不可。”
那是场荒唐的做爱经历。对方是比我年长十岁的女人。
禹加摆摆手,“你不想说算了,骗你做什么嘛。”
我没有搭理他,双手抱住脖后靠在墙上。那一年我只有十四岁,那女人二十四岁,一个年轻的钢琴教师,每个周末我便被母亲送到那学钢琴。
“十四岁学钢琴,未免太晚了吧?”
“别打岔!”
那女人待我极好,人也长得漂亮。她有着寂寞的气质,因为她总是弹悲伤的曲子并且泪如雨下。有一天她猛的把我抱进她怀里。我的脸紧紧地贴在她的胸部,我闻到了她的体香。她说,南西,你能让老师快乐吗?你喜欢老师吗?接着她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我那还是头一遭这么近距离地看见女人赤裸的身体,脸蹭地就红了。她微笑的替我解开衬衫脱去短裤,南西,你真的是个大人了呢。
“你们做了?”
“做了。”
我们一个月几乎四次这么做。其余我不在的日子就无法猜测她怎样度过。她说她要我跟她走,她说她能养活我。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学琴了,三个月后她也搬了家。也是打那之后我对女性有了莫名的愧疚。以后和我交往的女孩都无法和他们睡觉。
“当初为什么不和她走?”
“不知道。或许是担心她是少年诱拐犯。”
禹加嗤嗤笑,“那么现在有女朋友吗?”
“没有。等心理障碍过去后再说。”
实际上我还同三个女孩睡过觉,只是一要做那事时我便喊停了。他们一个是我高中的同学,一个是在游戏厅里认识的女孩还有一个是大一时通过朋友认识的,或许是从哪请来的三陪小姐也说不准。前两者的交往同时进行。
6.
在思考禹加回来时到底该做什么时我做了不少的事情。洗了放在水槽里的碗筷,把放在床上地上和角落里的脏衣裤放在洗衣机里清洗。中途接了一个电话,是在大学曾经听说是暗恋我的女生打来的。她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接下来该谈什么话题就变得尴尬,三两句话就挂了电话。给仙人球浇了水,整个地板都刷了一遍,把洗好的衣服漂干净后晾起来却发现衣架不够,从楼下商店买来衣架和泡面。大约五点时开始烧开水。晚餐就吃泡面。我已经很累了。
真是意外,今天果然是个全民忙碌的日子。
禹加五点三刻刚过就回来了。他说,什么事啊,这么急。
我东张西望发现昨天租来的影碟还在电视机上放着。“请你看碟,够意思吧。”禹加拿过碟片在手中晃啊晃,哼了一声也便没多说什么。
我俩就做在沙发上吃泡面看《活色生香》。这是阿氏典型的带有部分粗口和性场面的女性影片。
“我说你昨天就是拿这电影吓走苏乙的吧。”
我发问似的看着禹加。
“别装傻了,这是租给苏乙看的,对不?”禹加得意的扬起嘴角,“说吧,到底有什么事想劳我帮忙。”
“你以为你是谁啊,瞧你东的屁颠屁颠的。再说,这碟是她租的。”
“哦?!”禹加露出怀疑的坏笑。
“她昨天说她很累要睡在这,我只不过担心她的安全让她回宿舍,她就猛地哭起来了。就这样。信不信由你。”我把碗一放,走到电视机前按下开关。将碟取出来放在cd盒里。
“人家都豁出来了你还看不出来。你是真不懂还是真不想?”
“她要和我……?!”我迟疑片刻,“如果真是那样,我真是不想。”
7.
我仍有心理障碍。况且我对她没有冲动。我之所以和她在一起是个失误。不管怎样,我要向她道歉再提出分手。拖得越久伤得越重。
8.
禹加最近很早便出去了。打电话给海生,他说最近他也很少来酒吧。和他寒暄了几句之后就打电话给苏乙。接电话的又是那个江浙女孩,她说,不在不在!便又挂断了。这次她看起来更急。我不清楚她整天忙些什么,也许她月经期也来得急吧。的确有这种迹象的可能。诚然,暗地里咒骂别人不是个好习惯。
下楼开信箱取回两封信。一封是被某知名杂志社退回来的稿件,还有一封是没有署名的信。信封上写着“混蛋收”,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
“你别再来骚扰我了。混蛋!我看你八成是性无能。你这个无所事事的窝囊废。找个地方看黄河图片手银去吧!”
仍旧没有署名。但我知道会是谁写的。整封信明显有两种字体。我想苏乙这种女孩只写了前面的“你别再骚扰我”,而后面的恐怕是那个月经频繁的江浙人。不过那句“找个地方看黄河图片手银去吧”写的委实生动。
我边回味这句话边取出退回来的稿件准备寄给另一个二流杂志社。该做的事都办妥当后我便开始睡午觉。
我做了个古怪的梦。
我是一只外形丑陋的黑鸟,但我的声音动听。我四处飞翔试图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甜美的歌喉。但他们看到我的模样便仓皇逃去,还不时的咒骂我是个灾星。没人仔细听过我的歌曲。我只好在寂静的坟茔堆中嘶声呻吟,直到嗓子哑了,最后只能发出难听的哇哇哇哇。这次以后,人们给我起了个名字,乌鸦。
这个梦很有纪念价值。醒来后我花了好半天时间才能完整的想起她。
9.
禹加同很多女孩睡过觉。但他绝对不会把女孩带到我们的公寓里来。这点从一开始便达成共识。
他模样俊朗所以女伴也都挺漂亮。
毕业后禹加曾试着找工作但没有哪家对他这张二流大学的哲学文凭感兴趣。我说,你可以长期住下来。他拍着我的肩一本正经地说,好兄弟。
他一直想找一个既体面又挣钱多的工作。在平时生活中,特别是在女人面前。他从来不说“等我有钱了……”,因为这样会让人知道他现在没有钱。只有当他喝醉时他才会说这句话。所以每当海生听到他说时便叫我领他回家。
目前这句话他说过四次。
“等我有钱了我要分给南西一半,不,一大半钱!”
“等我有钱了我要买个市长当当,我要全市的市民都是漂亮女人!”
“等我有钱了我要盖个工厂!”
“等我有钱了我要将啤酒灌满整个游泳池!”
因此可见他目前醉过四次。细心琢磨,我发觉他的欲望越来越小。的确如此,我们要求的本质上甚少,能够生存下去便是欲望的基石。我想要告诉他他需要的绝非金钱,却总是丧失适当的时机。
10.
“最近都干什么去了?怎么老不见你。”
禹加愣愣的笑,“发财去了。走,请你吃饭。”
我想我务必要清楚这钱的来历。平时他偶尔赶场子,一个晚上唱下来顶多也就四五百块钱。这对他的消费程度来讲是不够用的。
“最近演出多得连酒也喝不过瘾。干脆去海生那喝酒得了。”禹加将放在沙发上的外套递给我,“难道我去杀人放火不成?是兄弟的就同我喝酒去。”
平时就很少去泡吧,海生见了我也不由拿我开涮。“你也想过夜生活了?”
“有不妥的地方?”
“没有,哪敢。”海生服务式微笑的端来两大杯酒。
禹加先灌上一大口,用手晃荡着酒杯,“南西啊,也许过一段时间我就得搬走了。”
“住着不习惯?”我两手握紧酒杯。
他摇摇头,“我就快有钱了。”
我点点头,将嘴贴在酒杯上。
“不问清楚钱是怎么来的?”
“没那必要。”
我看着吧台里手提式的电视机播放的节目,欧洲足球赛。虽然平时我对这毫无兴趣,此时却格外专注。他们那娴熟的技术让我明白为何中国队出线是那么值得庆幸。作为非球迷这么说似乎有些欠扁。喜欢看球员不停在球门前补射折磨守门员来满足自己郁闷的扭曲心态。隔了很长时间我们都不说话。
“什么时候走?”
“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禹加埋下头,“麻烦你这么久了,真有些内疚。”
“干嘛说这话,听上去特酸。”
我把视线从电视上转到门外,在移到门旁的单人座位上我看见一位约三十岁的女人,穿着漂亮的黑色连衣裙。她让我眼前突兀地闪过一个弹钢琴的女人的影像。
“禹加,我好象遇见熟人。”
“谁?”他立马放下杯子左顾右看。
“那个穿黑色连衣裙的。”我用眼神暗示禹加往门口的位置看。
禹加用目光搜寻了一番后笑着说,那人他认识,叫索麻,也是常客。
“她好象我以前说的那个女人。”
“哪个女人?”
“教钢琴的。”
“恐怕不是。”禹加挠了挠头发,“要不介绍你认识?”
禹加走过去和那个女人说了什么,那女人朝我这边望望,站起身跟在禹加身后走过来。恍惚中我好似看到走过来的正是我的钢琴老师,她哀愁地笑,她说,你能让我快乐吗?真的,太像了。可究竟我难以判断是否是同一人。
她先开口说话,“我们认识吗?”
声音在空中盘旋直到消失在某个尽头。我半晌答不上话来是因为他们连声音甚至语气都那么惊人的相似。
“我想我们不认识。”她笑容很浅可是很迷人,“我叫索麻。”
“南西。”
禹加知趣地走到一边和另一群人聊起来。
“说说看,我长的像谁。你的母亲还是你的情人?”
“想知道?”
“恩。想听。”她说罢用手撑着脸看着我。
我将她的样子描叙了一番。
她倒是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真不可思议,这连我自己都觉得像。我也会弹钢琴。可事实上我不是她。毕竟我和她名字不同,况且我也并不认识你。对吗?”
我将信将疑地点头。在一个多小时里我们聊了很多东西。我得知她现在三十多岁,去年和丈夫离婚,原因是她不愿意生小孩。目前单身,有自己的住房,早已不弹钢琴。最后她还留给我她的电话号码。
禹加在回家路上对我说,你不会对她有兴趣吧?
11.
我的那位钢琴老师叫辰砂。她总是弹令人哭泣的曲子。房间里没有照片因此她显得愈加形单影只。每次都是坐在我右边教我指法练习。隐约还能闻到洗发香波的味道。之所以总是坐在我的右边是因为她右边脖子上有一道两厘米的疤痕。
她不多话,也不经常出门。成天弹着不厌其烦的悲伤曲调。
她皮肤光滑而且带有好闻的体香。每次与我结合时会高兴的流出泪来。她想带我走,然而我逃离了她的世界。我一直觉得我和辰砂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是长期烙在我身上的罪孽伤疤。让我无法面对其他女孩。是她令我爱恨交加。
12.
傍晚我刚打开门就听见电话响个不停,来不及脱鞋就去接。一听那人讲话着实令我愕然。那个浙江人第一次用匀速度说话。
“你是南西吧?现在有空吗?”
“干嘛?”
“上次那封信你就当没看见,苏乙现在答应再给你一次机会。”
“那封信……你的文笔很风趣,我对最后一句比较欣赏。至于机会嘛,我想,我和苏乙分手会比较好。”
“你这人渣!小心便秘时从嘴里拉出来!”
嘟——
我无奈地看着听筒不由感叹这女人真赶上更年期。
过了一会,也就是我打了近两个小时的瞌睡时禹加带了一个男人回来了。我使劲揉惺忪的双眼却还是不太清醒。那个男人直径走到禹加的卧室里。我将禹加拉到一旁,我说你莫非真跟男人好上了?
他乐的大笑,不是不是,这是帮我收拾行李的。禹加勉强地笑着说,我到一富婆家当老公去了。
我盯着禹加不愿说话。我简直无法将他同男妓真正等同起来。
“别这样,我知道你会因此而看不起我。不过,我真的不想再过穷日子。”他声音哽咽,“我会给你来电话的。”
“不用了,我没那闲工夫。”
“南西……”
“走了也好,我好找个人买下这房子,一个人住太浪费。”
“别卖!别卖掉它,好么?”
那个男子拎着箱子从卧室走到门口示意禹加该走了。我走到阳台把仙人球端过来塞到禹加手上。
“这个送你,像这样耐旱的植物即使不浇水也不会死掉。”
13.
我坐在酒吧里喝得烂醉。
海生无奈地叹息,你醉了我叫谁来接你啊。
14.
两个礼拜后我在楼下看见了索麻。她从海生那打听到了我的住所。
“到外面吃饭吧。我请你。”
“不用了。我只想上去坐坐。可以吗?”
“当然。”
我让索麻坐着,平时家中少有客人来因此没有沏茶的习惯。
“七喜可以吗?”
“行。”
屋里空调几个月前便坏了。只有靠破吊扇呼啦啦慢悠地转着风。我们对坐在那里不知道谁先开口或该说些什么。我只好站起身从一堆cd里翻音乐唱片。
“我说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怎样?”
索麻放下饮料,“舒曼的也许会好些。”
“那就听《克莱斯勒曲集》好了。”
“恩。”
“现在为何不弹琴了?”我重新坐下来。
“也不是为什么特别原因,只是没有那种想弹的欲望。”索麻双手合十放在膝盖上。
“那现在你干些什么?”
“可以不回答吗?”
“可以。”
交谈又一下陷入停顿。索麻看挂在四面的图片。最后她的目光停留在黑灰红相间的人面像上。那是个被拉长的脸,秃顶且丑陋,胡渣稀疏。
“谁画的?”
“不太清楚,是从一条老巷子里低价买回来的。听说画中人是作者的父亲。”
“何至于这样丑化父亲。”
“想必是的爱的另类表达,不过如果是我,想必会将自己的父亲画成反町隆史。”
她笑着点燃香烟。点烟时她一直看着这副画。我看着她保持的姿态,她留给我一张左脸。这又让我想起辰砂。她也只给我左脸的姣好面容。我不由地企图猜她右边的脖颈是否有块伤疤。房间里充满夏日浓郁的色调。阳光透过门窗穿过卧室洒在她光滑的手臂上。紧身的棉布无袖衫突显出她仍旧性感的曲线。我坐在那心悸的大口呼吸。
她转过脸来。将烟掐灭。一阵长叹的烟雾绕开,渐渐消失不见。
“现在有女朋友吗?”索麻开口问到。
“没有。”我换了一种姿势,将左脚搭在右脚上,“不过倒是谈过几个。”
“有那种经验没?”
“没有。”我又迟疑了一会,“恩,没有。”我把辰砂的事故意隐瞒了。
她眯着眼睛看着我,用手指轻轻的剔掉残留在嘴角的饮料水迹。
“不想做?”
“不是不想,只是没那欲望。就像吃撑了后再看到山珍海味也没欲望似的。”
“那么,能否同我做爱?”
15.
我很久没有开信箱。里面被塞的满满的。
一封普通来信,两封杂志社来信,一张包裹单和一大堆传单。我在上楼的过程中将这一大堆传单大致浏览了一遍。两张商店降价消息两张搬家公司的四张性病广告。我将它们揉合在一起。顺手扔进楼道的垃圾通道。
包裹单是苏乙的署名。我想那里面一定装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村上的《寻羊冒险记》,另外还会有我的画册一个棕色熊刊登过我文章的杂志和一张我高中毕业时拍的那意气风发却略显傻气的照片。这些都是当时送给她的。现在她必须都还给我,就像所有情感泡沫剧里男女主角分手后那样,彻头彻尾的互不亏欠。
我坐在阳台上拆那两封杂志社的来信,竟意外的全是邀请函。我同时被一所一流杂志社和一所经常采用我稿件的二流杂志社邀请成为其编辑。将两张函书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有些迟疑。我看两封信的日期,后者比前者早四天。所以我认定了那所二流杂志社,其实这正符合我的心意。我把两张函书都压在桌子的玻璃板下,留做纪念。
至于还有一封来信,我看那字体就肯定是禹加写来的。
16.
索麻的身体与我想象的一样迷人,我对她的身体熟悉就总让我记起辰砂。我亲吻她的脖颈,发现她的脖后没有伤疤,只是光滑。我说,你真的不是辰砂吗?她说,其实有很多事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又曾不止一次的设想:
一.
索麻与辰砂是一对分开的双胞胎姐妹。
二.
索麻与辰砂不是双胞胎姐妹。只是分属两个生命体的两个人。
三.
索麻与辰砂是同一个人。只是两种意识存在于同一生命体。
四.
索麻与辰砂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由于某次意外使她丧失记忆,之后她改名换姓。至于她的伤疤则可以认为是做过美容手术。
她的那句“其实很多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确实诡异。
不管怎样,我已经没有心理障碍了。我喜欢的女子必须具备成熟,性感,气质并且单身而且历程丰富。
17.
在编辑部工作时意外的发现稿件中夹着那封禹加的信。好奇心使我不得不拆开,窥看内容:
“南西:
……你的电话一直拨不通,其实我真的挺珍惜你这个兄弟。这个夏天真是太丰富了(措辞有些奇怪)……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常泡吧的目的,可我发现我的目标逐渐缩小时我真的恐惧这种没钱的日子会令我窒息地死掉。我想做个有钱人……南西,如果你同意我们还是朋友的话请给我电话(号码写在最下方)
……我现在的生活挺好……最后,那个女人赞助的杂志社(名字是xxx)已经答应请你做编辑了,我想这应该是你喜欢的工作吧……
署名:禹加
某年某月某日”
当天晚上回到家,我从桌上抽出那张一流杂志社邀请函连同他的信一起烧掉。它们燃烧得如同涅槃。
18.
我换了一间很小的住房,原来父母留给我的那套房子是个价格不菲的遗产。我将它们作为积蓄存进了银行。生活又逐渐如同所有积极生存的人进入了正规。
就算雨天我也会忽略掉上帝的眼泪。
19.
偶尔去海生那将自己灌到快醉时步行回家。和年轻漂亮的女人搭讪,但绝不同她睡觉。我会找个固定的女伴,她还必须不在乎我的过往。夜生活是让人麻醉的最佳途径。白天我们又要委琐成安居乐业的工作人。其实终究我们都会回到各自的房间带上门睡觉。我从窗的缝隙中看月亮,自揣人类活着的终极意义。不停想着就不免觉得孤寂,宛如被抛至废墟中或是停在坟头的一只乌鸦,用沙哑的呻吟回应空虚。我们永远在黑夜中等待第二天,第二天究竟什么时候来,不得而知。也许有一天就会在等待中缓慢的死去。我惊恐地大喊,声音却似乎正默默渗到黑夜寂静的旋涡里去了。
|
|
|
我毫无个性
我只是社会主义好公民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