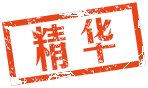我站在窗台边上,十月的凉风从嵌开的高大玻璃窗钻进这个空洞的房间。这里本来是万维商务的办公间。可是一周前他们搬到对面的大厦,于是这里在有新主人之前都会像现在这样,空荡荡的寂静无声。我上班的地方在隔壁。那里每天有几十个人两班倒,昼夜不停的接听那些不知从什么角落里突然打来的电话。
工作久了,有些声音会变得熟悉,可是每个人都清楚那些依旧是陌生人,因为这仅仅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电话在线的时候,大家会打游戏消磨时间。而我通常是写东西或者像现在这样,来这里抽烟。
没有人的地方空气总是新鲜的。我顺势坐在地毯上,靠着冰冷的墙在昏暗的光线中闭上了眼睛。
“原来你也抽烟。”一个轻轻的舒缓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我睁开眼睛——是爱菲。
“恩。习惯了。”我有些答非所问,然后莫名的笑了笑。我是个不擅长回答的人,从小到大。我总是对问题不知所措。这与我知不知道答案无关,我想我只是不习惯回答。
“《花开彼岸》是你写的吗?我挺喜欢的。”爱菲没有理会我的局促,径直的问。
“哦,随便写写的。”我不奇怪她看过,因为我们每天都坐不同的位置,她会看到那篇东西也不奇怪。可我奇怪的是她会喜欢。因为她看上去是那么明亮的一个女子。尽管我和她说过极少的话,可是她似乎总是在和周围的人热烈的聊着,似乎她身边永远不缺朋友,而她永远不会寂寞。
“阿黛,我特别喜欢《过客》里面那句——佛说,前世三百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她叫我的名字然后对我说。
我笑了笑,又点燃了一根烟“你相信宿命吧。”
“是的。”爱菲在我身边坐下,也点了根烟。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有些胖,却生得美丽的女子和我有什么交集。因为我注意到她眺望的目光似乎在看一场绚丽却不长久的烟花,而这样的人通常是过度自卫并没有安全感的。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她就那样突然在我眼前停下。
昏暗中,我递给爱菲一根骆驼。她吸烟的姿势很熟练。我们谁都没有看彼此,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任何动作就可以感觉到对方那些熟悉的气息。
爱菲的烟龄已经有十年了。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
可是我在她的脸上却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来解答我的疑惑,她平静得就像夜色中的湖水,没有波澜只有微微的凉意。
“你为什么抽烟呢?”爱菲侧过身,长长的睫毛在她白皙的脸上投下一道淡淡的阴影。
“不为什么,习惯了。”我说不出原因,只好给了她一个不像答案的答案。
“其实,我最开始是不吸烟的。我只是喜欢把它点燃,然后看它们慢慢的燃烧——那感觉仿佛有一个人在那里安静的听我诉说”。
我没有说话,一边看她吐出的烟雾缓慢的飞散在空荡昏暗的房间里,一边等她继续说下去。
于是,我知道了那个关于破碎和疼痛的忧伤故事。
但凡沉溺于香烟的女子都是落寞且隐忍的。但人们能看到的只有冷淡或张扬。世人觉得那些都是荒诞的叛逆,可是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在这之前,她们已经被这个世界背叛。
爱菲说——这是宿命。
我晃了晃烟盒,抽出里面最后两支烟,一支递给了爱菲,另一支自己点燃。
天气不断的降温,夜里冰凉的空气在我裸露的颈上掠过,仿佛一条条游移的水蛇。爱菲在给我讲一个关于等待的爱情故事。我伸开有些麻痹的腿,几分钟后,等待了几千年的女子在我眼前飘飘摇摇的笑着飞走了。最后,爱菲说,每一个与她相遇的男子都与她有宿世的情缘。他们的前世欠了她,所以要用今生来还,等到来世她再把她今生欠他们的还给他们,那么大家就互不相欠。这个叫缘定三生。
我笑着。
我不知道三生是什么,也不知道三生有多久。可我知道那一刻的爱菲是那么的伤感。
三天后,我离开了公司。没有告别。
断层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单调、灰色。牒片、香烟、睡眠像客厅里落地钟的滴答声一样滞重而冗长。爱菲没有我任何联系方式,她那张简短的字条像一只幽蓝的蝴蝶不断的在我模糊的意识中抖动它脆弱的翅膀——
171,我完了。我想我爱上你了。179。
我闭着眼。因为小时候听人说过,蝴蝶翅膀上的鳞粉是有毒的。如果进到眼睛里,就会失明。
但我最终还是去了,去找那只漫无目的的蝴蝶。
电梯停在七楼,走过拐角我看见那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有个模糊的人影。
是飘。
“阿黛,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她是我曾经的领班。声音轻柔甜美,并且有着与声音极不相副的率真与热情。
“哦,我回来拿点东西。爱菲在吗?”我已经意识到她并不 在公司,可我还是问了。
“她已经一周没来了,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她淡淡的说。
我有些意外,没再说话。走进工作室,大家都在忙着,看见我热情的招呼。那里是个很温情的地方,很多人会记得你,然后问候你。可就像我匆匆的离去一样,有人匆匆的来。爱菲不在。
我和大家寒暄了一会,收拾了简单的东西。给爱菲留了字条和联系电话。就在我要走的时候,有人说接到爱菲的电话,说她明天回来。
我笑着,离开了那个工作了十天的地方。
“阿黛,世间的很多事是无法解释的。我遇到朔西的时候突然明白了这一点。”
“朔西是我见过的最明亮的男子。”爱菲轻轻的说。
她们在网上相识了两年,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面。那天,她一个人在酒吧,突然想给他打电话。结果电话刚拨通,吧台旁边一个男子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们遥遥的看着对方,微笑着点了一下头。
“喂?”
“喂?”
两个人很有默契的笑了一下。男子向她摆摆手,示意她过去。爱菲没有动于是男子走了过来,在爱菲面前坐下。就像所有熟悉的陌生人第一次相见,他们没有太多的语言。两个人抽烟,说很少的话,那些熟悉的思想和味道在空气中无声传达。
后来,朔西告诉爱菲,如果她可以跟他回南方,那么他们到那边之后立刻结婚。
朔西走了,爱菲留下了。故事变成了泛黄的相片,被她压在了箱底。
爱菲终于联系上我。
在中兴门口寒夜的冷风中,我从背后望着那个熟悉的背影。她突然转过身来,对我微笑。她告诉我,她去了山东。想留在那边,可是最后还是回来了。
她在讲的时候我依稀看见那些陌生的城市街道、陌生的人群和陌生的自己。这与念旧没有关系。人们只是习惯在那些熟悉的地方寻找安全感,哪怕那并不是你喜欢的地方。
在一条很窄但灯光很明亮的小巷里,爱菲挽着我的手臂用电话和朋友告别——她刚刚辞掉了工作。原因是和刚上任的主管吵了一架。她挂掉电话侧过脸看我——你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吧。我笑着点点头。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爱菲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路灯的光不断的在她白皙的脸上滑过。有种恍惚的感觉。“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你是个男人。可有的时候我又不希望这样,她们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依恋你。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愿意把我从他们带来的伤害中拯救出来的人。”
“如果我是个男人,结果是不会变的,变的只是伤害的形式。”我回答爱菲的自问自答。
下车后,我们站在马路边。她等一个男人。我等那个男人把她接走。
在那段被记忆渲染得浓重而难以分辨的情感中,他是她心头的一个美丽泡沫。她留恋的不是他,只是他带来的那些关于爱情的泡沫。就像饮水思源,她还是忘不了那口曾经甘冽的井。
感情是悬在头顶的双刃剑,至少是要有一个人受伤的,也许是两个。
我站在路边破败的护栏上,护栏很低很细。我努力保持着平衡。可我总是从上面掉下来。爱菲说,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找到支点的,因此我们无法平衡什么,努力的走或者停止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掉下来。
半个小时后,爱菲被那个男人接走了。我远远的看见他的身影,30秒后就消失不见。
也许一个人真正可以停留的地方只有另一个人的心里,而他的就是爱菲的。
我最终还是没学会平衡,从护栏上掉了下来。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爱菲是小时候的样子。事实上我不认识那个孩子。可是我的梦告诉我,她是爱菲。
小爱菲坐在学校空荡的教室里。在很多桌椅中见,她低着头。干净的木质桌面上有一支点燃的香烟,爱菲看着它慢慢的烧。然后开始流泪。
爸爸是有很多女人在身边的那种男人。妈妈是固执得可以把爱变成恨的那种女人。爱菲是个不会在人前哭泣的小孩子。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般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渡一切苦厄 。。。。。。
依般若般罗蜜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盘 。。。。。
我开始念心经。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是湿的。
那个时候开始我突然意识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生活中一直走着各种各样的女孩。她们带着笑脸和伤口望着我,而我也不知不觉的望着她们。ivy这是她的英文名字。意思是长春藤。
我想起那个关于垂死的病人因为一片长春藤叶而活下来的故事。于是我问,如果没有人画上那片叶子,他是不是要死去。那常春藤又是靠什么活着呢。
“我希望王子和公主最后能在一起。”爱菲对我说。
我不知道王子在哪里。我也没有任何像玻璃鞋那样美妙的线索。我只是希望她快乐,可我的希望比王子的消息更渺茫。
突然有一天,爱菲对我说她要离开这个城市,她要去那些没有往事的地方。隔着电话线,我说——好的。
而那些更多的就像所有留在心底的话一样留在了心底。
爱菲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行。因此,在我的生命中爱菲真实的在我的面前出现只有两次。一次是哪个一起抽烟的夜晚,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断从护栏上掉下来的路边。
我想象着爱菲握着胸前那块玉牌登上远去的列车的样子。她曾经对我说过,那块玉很灵验曾经帮她赶走了一只鬼。我笑着,想象她留在那上面的体温。对着电脑不停的打下s。屏幕上是一串串的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生生世世。
两年后,爱菲来信,她和一个在阳朔认识的大她12岁的男人结了婚。她带着他们的结婚戒指走过了很多山和很多海。看了很多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她说,那个时候她才明白最美的不是花开而是花谢,因为这意味着最初的新的开始,最感动的也不是潮起而是潮落,因为它象征着最终的平缓的安详。
我想,在她的窗前真的走过很多骑士可其中只有一个才是真的王子。而她也是找的到王子的,因为她才是真的公主。
|
|
|
冷冷的一切已经走,冷冷的一切会再来。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