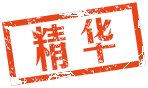一个穷苦潦倒的大学生的日记
太阳落下来了,稍微带着点柔情,我的皮肤开始隐隐发痛,大约是紫外线不懂得虚伪。微风在挑逗,挑逗地面的灰尘,也挑逗两片肥厚的树叶,树叶轻轻地摆了摆头,表示拒绝。空气的成分还没有失调,因为花园里的青草还在扯长劲子疯长。参差不齐的绿生机勃勃,使我联想到了故乡那片青色的山坡,还有那个背着竹篼割草的小女孩。地面十分潮湿,这正是夏季。
我走在大街上,并不招摇,还戴着一个学校的校徽。路很长,这种感觉完全因为重重的脚步无法在坚硬的水泥地面留下一个脚印,于是我沮丧。迎面一个摩登女郎款款而来,撑着把漂亮的花伞,与我几乎擦肩而过。她没有高过我,尽管她的鞋垫足有十二厘米。其实我只有一米七四。她看了我一眼,有点莫名其妙,我感觉锝出来,而且我也知道,她不是恭唯我的英俊,而是对我脸颊下边那颗在汗水浇灌下更显绯红的粉刺疙瘩甚表关注。
湿漉漉的,一张人民币,散发着十元的热气。
握住了幸福,空气好稀薄,明天是一个人的生日。
离奢望不远,有送给他的礼物,亲切而且贫脊。
回头望呵,自行车偏离了方向,却靠近了本质,比如摔倒在荒野。
大雪凝固,好象堆积稻草,花白花白的稻草,一个人走进一条小巷。
这里很热烈,不仅仅因为有大家和小卒。
月光如水,洗白了黑暗的思想,无比辛苦。
为了明天不孤独,他用积蓄起来的苍凉换取一本书。
书名可以不确定,但那张人民币必须有湿漉漉转为干涩,最后枯萎。
穿梭的梦幻,承栽不了尘世的顽固,水面无波,鱼在倾诉。
这个人幻化成了我。
其实书名可以确定,就是那个与宋朝农民领袖同名,中年就夭折的教书匠的文集。为了读取方便,我们暂时叫它《王小波文集》。我走进一条小巷,理由很简单:用身上仅有的十元钱买本书,以此来排遣生活的无聊。人们给复制别人的东西而不给手续费的行为起了一个雅俗共赏的名字,叫盗版。所以我买的书也是盗版。
“小兄弟,买书啊?”一个满脸雀斑的妇女表现出一种非职业的热情。
“随便看看。”与其说我在看书,不如说我在看她:腊黄的面庞,两只空洞而平乏的眼睛深陷进去了,犹如一堵斑剥老墙上的两个破洞。说不定她又是一只被世界遗忘的羔羊从某个国家工厂出来,失去岗位的双手和大脑只有操起这门行当经营,聊以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我最擅长于悲观的猜想。
“都是些新书,值得看一看。”她似乎有点疲惫,但不颓废,可能我对颓废有一种敏感,习惯性的敏感。比较幸运,今天没遇上那种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的男摊主,他极力向你推荐所谓的畅销书,譬如《安妮宝贝》、《古龙全集》、《外国情爱小说》,其咄咄逼人之气势实在让你轻松不得。
书找到了,在摊位的左下角,除了尘埃,封面还写满几许羞涩。
“我要那本。”随着我指的方向,她疑惑地抓起那叠由厚厚纸页集合而成的标本递过来。错别字不多,一页就两三个,我很满意。
“多少钱?”
“十五块(元)。”
“太贵了。”
“那十三块。”
“不行,十块,咋样?”
“小兄弟,十块我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这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无论如何也得十二块。”
“这种书纸张不好,错别字又多,给十块你也是有赚头的。成本就那么几块钱。”
最后,她屈服了,这本书以十元成交。
手伸进口袋,我准备触摸并掏出那张湿漉漉的人民币。空的 ,不可能!翻遍所有的口袋,没有!再摸摸,还是没有。这怎么可能?事实上,这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成了现实。
汗水,冷的,没有从额头冒出,流进了心里。
很清楚,拥有三只手的动物嫉妒清苦,它们涂满毒酒,在自己的手上。
暗箭,对准一个目标,他不哭泣,面带微笑。
那是个婴儿。
回来,蚯蚓,沙土里有雨水。
比较糟糕,雨水里饱含酸碱,还有香甜。
蝉喜欢躁热,柳荫下,破碎一只耳膜,没流出血。
捂住鼻孔,花儿正在开放。
动用两种感官,会惊醒田里的青蛙。
喝杯白开水,润润沉默以久的喉咙,脏话快活起来。
词语很多,全都躲在草丛里乘凉,缺乏诗意。
叹息,比哭泣更千娇百媚,欣赏美,毁灭在音乐的怀抱。
划破长空,星河突然暗淡,蝙蝠拍了拍翅膀,中断遥远的梦幻。
路 ,继续坎坷,尽管没有脚步。
其实,我已把脏话说出了口,虽然我没有喝掉白开水。“操!”我很冲动,很愤怒。但我开始后悔,我已背叛了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不冒出“草尼玛”这样的传统国骂?如前所述,我用来为自己准备生日礼物的十元钱被扒手摸了。明天,我二十一岁,我有点悲伤。
大呼小叫、逢人诉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别人告诉我:这是e时代。我沉默下来,习惯性地。要不然扯长鹅颈看热闹的过客和冷嘲热讽的声音就会聚积起来扑向你,火辣辣的疼痛和冰凉凉的寒心足以燃掉你所有的尊严和良知。古人说:“沉默是金。”
“不买了。”带着无限的惆怅与失落我仓惶逃离。“莫名其妙!”这声音很熟悉,大概就是背后那个摊主针对我的出尔反尔说的。声音搀和抱怨。
城市里依然奔跑着汽车,红色的出租车叫Taxi,白色的公交车叫City boat。可我怀疑它们是沙漠里的海鸥,飞呀飞,永远也飞不出喘着粗气背驮亟待减肥的人们的命运。就象春蚕,注定要在晚年为自己营造坟墓钻进去一样,崇高而无奈。到哪里去,这问题我想了半个小时。要知道这三十分钟银河计算机进行了多少亿次运算?回寝室,满屋子的脏衣服、臭袜子夹杂着肆无忌惮的“自由言论”,不能让你窒息,也会染上疯牛病。拿起英语书到教室背四级单词,刚走到门口,“本教室下午有课”几个并不美观但很遒劲的粉笔字只好使你走开。另外找找,好不容易觅到一间人烟稀少的,走进一看,场面又颇为壮观:几乎每个座位的桌上都躺着一本诸如《高等数学》、《现代汉语》、《计算机维护》、《化工分析》的教材。它们都瞪大眼睛用傲慢的神情盯着你,意思是说:“本座位主人已预定,请走开!”那么到操场打篮球,这项运动不仅要经得起累,还要经得起踩。对方穿着双星足球鞋来驰骋篮坛,你时时得小心,稍不留意你的脚板就会被碰上一脚,不很痛,但保你用正常姿态走不了三步。
最后,我去了江边。写到这里,我写不下去了,脑子陷入一片混乱。因为根据逻辑判断,我去不了江边,不是路途遥远,也不是半路出了车祸等问题,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条江。但我至今记得,这条江叫嘉陵江。没有这条江就没有下面的故事,没有下面的故事就没有生活的荒诞与离奇。所以我抹杀了生活,抹杀了这条不大不小的河。当时的情景是这样:阳光强烈、炽热,辽阔的江面波光鳞鳞,显然是受了微风的吹拂。泥土的气息混合着涩涩的青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高大的杨槐树的白色的小花悄悄发出沁人心脾的郁香。我躺在树下,这里有一大块阴凉带,很适合疏松僵硬的躯体和展开见不得人的联想。屁股下面的杂草很结实、茂盛,给人一种凉凉的和痒痒的快感。于是我又联想到了故乡那片青色的山坡,还有那个背着竹篼割草的小女孩。抬头望望天空,云朵很少,灰蓝色的底板一铺万里,决不吝啬。我记得一位诗人这样写到:钢蓝色的夜空下,无数天才在行走。我不是天才,所以我躺在灰蓝色的天宇下,有时还用眼睛瞅瞅水里,看能否发现高大的杨槐树和雪白的云朵。但失败了,江水很浑浊。
扯一把野苦蒿放在嘴里,我开始打盹。我敢肯定,我没有睡着。“啪”的一声,无比响亮,我睁开眼睛:天啊,我面前躺着一条足有一米长的大鱼,全身金黄,还蠕动着两腮。这怎么可能?难道它从水里跳上来的,那它又何必呢?它说话了:“好心的有缘人,救 救我,救救我!”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惊讶,只有目瞪口呆。最后喃喃道:”救你……”
“对呀,我快没命了。那伙渔夫快追上来了,我肯定要被抓住!”它掉泪了。“你怎么会说话?你是条鱼啊!”看见鱼流眼泪,我感动极了。“这一切都解释不清楚,你快把我抱到树林中藏起,直到那艘渔船撒网过后,我会告诉你真相。请相信我!”它又掉下一串滚圆的泪珠,落在沙地上顿时被沙土吸干。恕我直言,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鱼流眼泪,更没听见过鱼说话。今天这一遇,让我油然而生“不枉走这一遭”的感觉。隐隐约约,耳边响起马达的声音。越来越近,是捕鱼的船只,这不用怀疑。随即江水荡起了阵阵波浪。
现在我面临三种选择:
A:把鱼藏在树丛中,以待后况。
B:袖手旁观,看鱼入网。
C:抱起鱼跑进农贸市场,卖个好价钱,也可弥补我今天的损失。
其实还有第四种选择,就是把鱼扔进水中,看其命运造化,任其自生自灭。通常人们采用的就是第四种方法,比如工商局从贩子手里缴获大量国家珍稀野生动物、蛇、青蛙等,然后就把它们放归大自然,场面颇具人情味。据动物们介绍,它们被放生后一般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流浪,然后又被捉到市场上,如此循环。
何去何从?我有脑子,我也在想。“这是不是一个骗局?救生固然高尚,可我会不会重蹈东郭先生的覆辙?”遇到的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你还要介入?”“自己向来就是自私的,有没有必要让自私继续下去?”“我很可怜,可一条鱼更悲惨。世界崇尚弱肉强食,但世界也应该存在同命相怜。精神的沦丧较之生命的剥夺,哪个更重要?”马达声越来越大,依稀听见了渔夫的喧哗。我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宗教,这与平时行为懒散,不好思考的我极不相称。自然,这时那条大鱼还在流泪,还在把泪水渗进干涩的沙土,偶尔痛苦地挣扎两下。我,又闭上眼睛,躺在结实茂盛的杂草上--等待渔船的靠近。
树上滴下一团鸟屎,稀拉拉的,正好落在我的眉心上,我没去揩它,反而微笑起来。
人类的行为真是无法解释,包括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也无济于事。其实又何必硬要去剖析它呢?能够用规律来表达的行为那不就成了机械运动?言归正传,轰隆隆的巨响已粗暴地包围了我的耳朵,波浪有节奏地拍击江岸,发出“啪啪”的声音。我猛地跳了起来,仿佛心脏受了电击,径直走到那条大鱼面前弯下腰抱起它在树林里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比较浓厚的灌木丛,我把鱼扔了进出,它被树枝猛击一下,掉在残根败叶上。我也钻了进出,颤颤兢兢地感受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好象那群渔夫要捉的是我一样。闭上双眼,我脑子里出现了革命战争片中鬼子进村扫荡的画面,硝烟弥漫,枪声不断……
马达声消失了,它们在抛锚?
“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折腾了变天,捞他妈点小鱼虾米,还不够老子的下酒菜!
“鱼都死绝了吗?照这样子只有喝西北风了!”
“还要养家糊口,一家三只饭碗装啥子哟!”
“咳,鱼都打光了。”
“打光个屁!全是那些化学厂造的孽。你看这水,鱼还能活吗?”
这是那群渔夫的对话,我虽然慌张,但还是能听见他们注满激情的高分贝的嗓音。
〖蝎子〗
随波逐流,托起几根漂木。
奔跑的水草,绊倒在蝎子的须上。
蝎子死了,无声无息,它没听见水草的哭泣。
忘掉生活,就象种植一株青稞,酒杯交错。
荞麦地,野兔疯狂,咬伤两只土拔鼠,吮吸没有血肉的灯光。
太累了,远古的化石说。
沧海桑田,鸡鸣桑树颠,紫红的桑椹果。
拔开废墟,发现了爱情,写在一只蛐蛐背上。
残缺的木简,记载着刀剑磨合的火花,春风习习。
马达声又响起了,他们在起航?
刚刚有点平静的江面又荡起了起伏跌拓的皱纹,比饱经风霜的老人的额头更丰富多采。这个比喻也许有点不妥当,这没办法,我读的书太少。直到今天,我才从图书馆借出几本中学就该阅读的书籍,可人以成年,思想复杂,那份开卷饱览的闲情逸致早以没有了。他们是走了,没有带走什么,这反而使我感到几分失望。低头看看旁边那条大鱼,一动不动,我以为它死了。大概是刚才我重重的一扔,在树枝和地面的撞击下它脑震荡或者肋骨摔断而命丧黄泉。那它也太软弱了!拔开厚厚的树叶,我钻了出来。阳光依旧强烈,江水依旧浑浊。逮住衣袖揩了揩眉心的鸟屎,我骂了起来:“该死的菜鸟,缺德的杂顿时树上发出几声怪里怪气的鸟叫,仿佛是对我的还击。小时候我和领家孩子爬上桉树掏鸟蛋的时,旁边的母鸟发出的便好象是这种声音。不过我们不懂鸟语,不然听懂了不是摔个半死也会气得吐血。咦,另外好象还有蟋蟋嗦嗦的声响,我缓缓转过头去:天啊,那灌木丛中站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身着金黄色的连衣裙,披肩的长发乌黑发亮,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这怎么可能?!我惊呆了,差点没晕过去。幸好我是个无神论者,头脑中最后一丝清醒和理智使我吐出一个字:“你是鱼--”“我就是那条鱼啊。”她微笑着走了出来。
“你是鱼--”我这句话完全没有经过中枢神经。
“对呀,谢谢你救了我。”
“我救你--你没死?”
“虽然刚才你摔得我很痛,但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真是刚才那条鱼?”
“那还有假!”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灌木丛,拔开树枝看个究竟。她开心地笑了起来,声音不象鬼哭狼嚎而象风铃摇曳。真没那条鱼,对于这个发现我既心安又不理得。稍微镇静了些,我说:
“你不会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吧?”“是啊,你真聪明。这不是传说,这是现实,你都看见了。”她回答。
“可我不敢相信。”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已经存在。‘存在即合理’,这是你们一个哲学家说的。”
“你从哪里来?”
“这你不用问,譬如你遇见一个陌生人,你能问他‘你从哪里来’吗?”
“那倒是,可我搞不明白,你是条鱼,为什么要说人话,要变成人的样子?”
“这正是关键,你想想,我不变成人的样子,不学说人话,我能活到现在吗?
“能否可以说,你能活到现在完全是变成人样,学说人话的结果?”
“那倒也不是,一部分原因应该归结于我对存在的怀疑,就象你一样:怀疑我的存在。”
“你怀疑存在,意思是你怀疑生活?”
“不错。对生活的怀疑导致我的苦苦思索,直到现在,可最终一无所获。”
“其实你获得了,你获得了你的存在。那另一部分原因呢?
“另一部分原因就不好说了,因为你是人类,按理我应该避讳。”
“但说无妨,我是人类的叛逆者。对此我很感兴趣。”
“你知道老鼠为什么能延续到现在,而且数量比人还多?”
“它们厉害呗!”
“不是,是因为人类厉害。你们用智慧和双手制造了工具、房屋,还有许多食物,你们除了会劳动外,还会在劳动之余用各种武器进行掠夺性和灭绝性的厮杀。黑名单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老鼠,因为只有它们才和你们抢粮食。最后你们失败了,广岛的原子弹毁灭了无数高级生灵,却没有炸死地下的老鼠。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们是侵略者和破坏者。受害者会历史地成为英雄,这已不可辩驳,可惜你们永远也认识不到这条真理。”
“据我所知,广岛的原子弹不是针对老鼠。”
“听我把话说完,黑名堂中没有人类自己,这个简单的‘人’子写在名单的背面,而且写得相当大,把整张纸都涂满了。等到消灭了一个物种,你们便用小刀把它的名字从名单中挖去,物种不断减少,名字不断减少,自然那张纸也被挖得千疮百孔,背面的‘人’字早也仅存点墨!”
“等到把名字挖完了,‘人’子也挖完了,是吧?”
“你说呢?”
“可老鼠还健在,且数量颇多,这是为何?”
“这是因为挖字的人还没耗完力气,还在作手足舞蹈的挣扎。你说你是叛逆者,我并不相信。你冲其量只是个退化者,一个退化成了低级动物的变种。比如刚才你救我。我看得出来,你完全不是出于对高尚道德的追求,不是出于对自身责任的维护,而是出于一种动物的本能。”
“你污辱我?”
“我没污辱你,相反我还很欣赏你,甚至有点喜欢你。”
“这不符合逻辑。”
“但它贴近本质。”
“好吧,既然你说它贴近本质,那我也想贴近你的本质--我能摸一摸你的头发吗?
突然之间我闪出这样浪漫的想法,全然忘记了礼仪之邦的规矩和自己的原始意图。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为你的举动付出代价。”她说。
“什么代价?”
“以后永远也见不到我。”
“这没什么,我能接受。”
“我为你的回答感到后悔,本来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她很失望的样子,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变得忧郁起来。
完全被好奇奴役的我轻轻地走近她,我没敢正视她那双忧郁起来但很美的眼睛,所以站在她的右侧慢慢神出手。有一首流行歌叫《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当别人唱起时我总想捂住耳朵,可此时我多想歌声能再次响起,哪怕是由最蹩脚的嗓门发出。我的手触到她的秀发了,柔柔的,软软的,非常光滑,似乎还有一股迸裂而出的弹力。呼吸一下空气,我的鼻孔填满了她醉人的发香,心里,则流入一丝很难把握的温馨。我认为,睁着双眼感觉这份温馨是一种浪费,于是悄悄关上所谓的心灵之窗。世界很安静,世界睡着了……
又一声鸟叫,吵醒了我没有入眠的安睡,我稍微打开一下眼睛:啊,她不见了!无影无踪,只留下我的手在半空中悬着,有点狼狈。我痛苦地叹了一口气,这才明白她最后一句话的涵义。可一切都晚了,我真的后悔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我那么自私,那么愚蠢?
苦笑着摆了摆头,我对自己说:“继续后悔吧!”
〖黄昏〗
青山隐去,曲线被拉直,水天相吻。
羞涩的姿势,沾满露水,企图打湿干净的海盐滩。
骆驼瞥了一眼夕阳,继续行走,背影长长。
划破血管,岁月流金,映照在黄昏。
乌鸦翱翔,欲与苍鹰比高。炊烟袅袅,不作评判。
月光采掘的联想,还飘荡着梅花的芳香。
白鹤啄伤风景,俯首低吟红彤彤的诗句,涛声依旧。
煮一鼎蝴蝶,匆匆祭祀美丽的祖先,虔诚的神态,直奔脆弱的心房。
夏雨,淅淅漓漓,把气氛抛给了冬雪。
自己提着灯笼,遍街寻找失散多年的记忆。
天色真暗下来了,比老虎还厉害的太阳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留下几块铅灰色的乌云在那里左蹦右跳、故作潇洒。风变大了,变凉了,我毛孔里的汗轻而易举地被卷走了,头发随着劲风上下翻滚,摇摆不定。望着卷浪拍击、暮色笼罩的江面,我内心升起一样酸酸的东西,名叫沧桑。要下雨了,我得离开,离开这片不设防的土地。毕竟这里不属于我,就象豪华的大观园不属于林黛玉一样。
拖着疲惫的双腿和晕晕沉沉的脑袋,我踏上了归校之路。我不时回过头去,试图把浑浊的江水、高大的杨槐树,还有流动的夏风装进眼睛里,待到即将忘却的那一刻把它们重新倒出来,再细细品味。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城市当中,但耳边似乎还响起浪击彼岸的声音--啪,啪,啪。人们晃动的身影在我面前呈现又消逝,消逝又呈现,大家都在忙着自己该忙的事,走着自己该走的路。当你正做一件事而不认为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快。因此朴素而不宏伟的校门出现在我视野时,我才明白我已经赶了一个小时的路。瞅着黄昏中的学校大门,一股暖流悄悄弥漫了我的全身,这是家的感觉,亲切、舒坦。
尽管每天有无数肮脏的事物在这里诞生,尽管我讨厌这名不副实的“人间天堂”。低头穿过女生宿舍门前的过道,我直奔自己的寝室楼。因为这儿栏杆旁站满了许多身着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通亮,头发梳得溜光的师兄。他们正在等待自己的情侣从里面风姿摇曳地出来,然后手挽着手一起走向电影院、溜冰场。
“路离,路离!”有人在叫我,转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班的组织委员兼通讯委员张琳。她从书包掏出一个白色的大信封给我,“你的信”,说出这句话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如动物学家在原始森林观察毒蛇交尾一样神秘。她走了,我也回到了寝室。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正在摆弄他的“朋克时代”,在使人神经发烫的摇滚电子乐中我打开这封来自我暗恋了很久的“行云流水”(这是她在校报上发表蹩脚诗歌用的笔名)的信。全文如下:
路离同志:
很高兴能给你写这封回信,你的九封情书——可能是吧——我已经全部收到了,这你可以放心。但我把它们看九又二分之遍,还是看不明白。拜托,下次(如果还有下次的话)能不能不那么深奥。还有,你能不能穿一双象样的皮鞋,你那双满目疮痍的皮鞋总让我联想到你的脸,这使我感觉很不舒服。
近祝:
夏安!
行云流水
2001.6.8
|
|
|
只嗅到一丝淡淡的血腥
刀已落下
|
|
|
|
|
|
|